进了胡同,再走上5分钟,才能到行李的小卖店。
小卖店长约3.5米,宽约2.5米,摆上床、货架、书架、小桌和一架古琴,剩下的空间只能侧身通行。
但这间小平房却大大有名,因为它位于北京二环里,等待拆迁。更有名的是它的所有者,行李。
行李毕业于民族大学的人类学专业,北京本地人,手里有着几套北京东城的老房子,算得上是名副其实的“拆二代”。
几年前,他辞去了图书编辑的工作,上了武当山当起了不收分文的义工,最后又回到小平房开起了小卖部。
有些人好奇他的故事:拿得出手的学历、价值近亿的房产,为什么还要去武当山“修仙”?为什么最后开小卖部维生?
行李把自己辞职后的经历写成了日记,发在了各大社交平台上,一时间成为了“网红”。
记者、摄像师纷至沓来,这让他有点困惑:当义工、开小卖店不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吗?
渐渐地,行李明白了。
在不敢任性的时代,太多年轻人渴望着行李式的生活——它未必精彩,但活得像自己。
当人人习惯了委屈度日,行李依然保留着一份单纯:将所学的知识和真实的生活结合起来,虽然代价不小——35岁了,行李依然单身。
这是一个人的、漫长的人类学之旅,痛苦也罢,沉醉也罢,一切都特别真实。
以下是关于行李的真实故事:
01
来武当山当义工后,行李才发现,原来并不是每个道士都身怀绝技、精通奇门遁甲。
在道观办完义工入职手续,道长安排行李在太和宫的“金顶”扫地,还嘱咐他一句,
“你在这里,每天会接触到大量香客、游客。也许你会从中看到众生百态,看到不一样的人生。”
不就是个烧香拜神的道观,还能见到些啥妖魔鬼怪,行李心想。
但在武当山呆了三天时间,行李就觉得之前30年都算是白过了。就比如,他之前从未想过“香灰”居然是寺庙里的抢手货。
有一次,行李在大殿值班,身边一个游客忽然叫做他问,
“你能不能给我搞点药?”
行李当时就愣了,后来才知道这“药”是香灰。
打扫时,有些游客会突然喊住行李,让他帮忙给自己“加持”一下——在游客疼痛的胳膊拍打几下。
即便行李推辞说自己不过是义工,对方也不管,
“只要是庙里的人都行,都能加持”。
甚至还有游客带着口红来武当山,要求行李给他女儿印堂按个红印,说是可以帮忙增加姻缘。
不夸张的要求,行李大多都顺手“加持”了,反正对方也就是求个心安。
最烦的是那些喜欢乱敲钟、乱扔硬币、在文物上乱涂乱画的人,有次行李还遇到一些人来做法事,上千人堵在山顶,把游客下山的路也堵死了。
行李把在武当上的见闻都写到了日记里,日记里还出现最“考究”的扔硬币者:
围绕金殿每隔一米就放一次,5个1元的+1个5角的摆一摞,不知道这是在摆什么阵法。
每隔几天,义工就要用竹竿绑住磁铁,把缝隙里的硬币吸出来。上百斤的硬币要由人工搬运到山下,送进功德箱。
行李是在2019年10月决定上武当山做义工的。
那段时间,他刷朋友圈看到在民族大学一同修人类学的学妹晒了张照片,配文是
“在这里扫完地就可以晒太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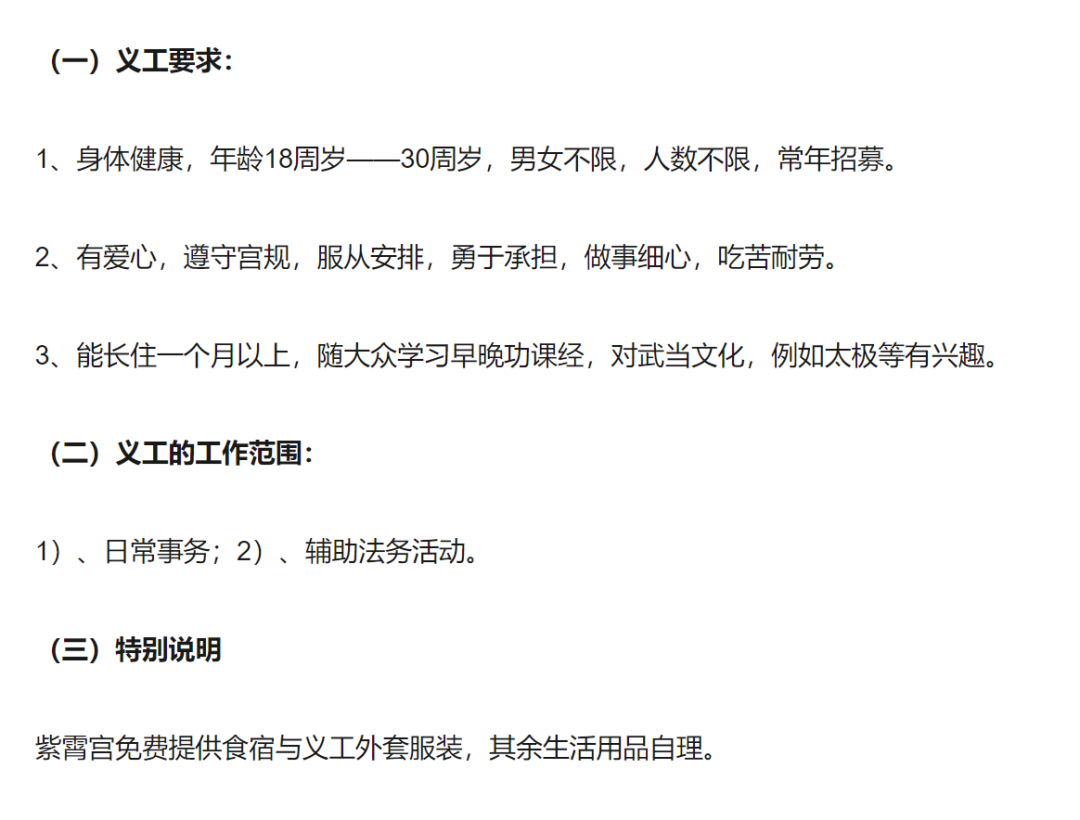
图 | 武当山紫霄宫义工说明
再一刷,学妹发的朋友圈大多是在武当山上“逗猫、喝茶、上早课”。
他开始幻想学妹的生活:
晒着太阳发呆,散步,看道长们练剑弹琴;每天按时到斋堂吃免费的三餐,中午可以有数个小时的午睡,等天黑后各回各屋“炼丹”。
或许,武当山这座幽密道观里还住着仙风道骨的道长们,他们在苍松古刹里静听晨钟暮鼓,闲看云聚云散。
日子清淡如水,彼此之间老死不相往来,甚至还幻想会不会有高人教掐诀念咒,或者其他什么奇幻的际遇……
“这不也就是我想要的生活吗?”
行李很激动,开始研究起如何去武当山做义工。
申请义工只要网络报名,对方在线询问几个问题:会不会书法、弹琴、新媒体、木工活?
行李只想做最简单的义工,就回复什么都不会,也没提自己是西南某民族研究所的人类学硕士生。没想到,即便如此,行李也很快通过了面试。
他本想上山就猎奇一小段时间,过过悠闲的生活。
然而,实际情况是,
“我以为我躲进了一片净土,而实际上却又被卷入了尘世”,行李的日记里写道。
02
武当山给每个义工都提供了住处,只要住进来,就管你温饱。
居住条件一言难尽,屋里常有毒蛇出没。
在武当山的一年多,行李见过金环蛇、银环蛇、手臂粗的蟒蛇,还有些蛇是游人偷着带上山放生的。
但也是在武当山的这段时间,让行李发现了知识的快乐。
古有名曲《梅花三弄》,行李原来听不明白,这么普通的梅花有什么值得歌颂的。
到了武当山,他见到真正的梅花后,终于懂了,
“人在山顶,被冻得跟孙子似的,看啥都美”。
再比如,看金庸小说,行李不明白为什么明教大举攻山时,要挑轻功好的人。来了武当山后就知道,登顶不易。
从山下坐车2个小时才能到缆车点,再坐20分钟的缆车、步行10多分钟,才能到金顶,轻功不好怎么上得去?
人世间的大多美好只存在于自己的幻想和朋友圈。
行李最害怕武当山的春天,那时候臭大姐(即椿象)成灾,出门都不敢张嘴。
直到最后,行李结束义工生涯回到北京,收拾衣服时还发现了两只跟随他几千公里的椿象,只是早已成“虫干”。
和行李一起来武当山的不少义工,都受不了苦走了。有的人来了,第二天又走了,也没人拦着。
道教不劝人出家,出家与否全在个人。
在修行者中,行李见过有人因工作不顺利出家、有人因创业失败、还有人因从小受家人影响……各种原因都有。
在传统社会中,道教为底层社会提供了慈善功能,这是书中很少提到的。
和行李一起到武当山的一名年轻人,父母双亡,他是来修行的,但学历不够,表现也不太好,可道长还是收留了他,道长说:
如果他们都不要他,社会就更不要他了。
或许是早年吃过苦的缘故,武当山的道士大多谦卑。
道长常提醒行李,如果遇到游客来磕头,一定要给人家敲磬,说两句吉祥话,
“他们没有帝王师心态,发自内心地觉得吃十方供养、应该回报给大家”。
行李研究生读得是人类学,当初来武当山还有一点“探索文化多样性”的私心。可遇到这些事,他还是会觉得这些无理取闹的游客让人愤怒。
有次一位游客沿着大殿周围撒香灰,被工作人员制止了,把游客急得不行,他说自己是某大仙派来解救众生的,现在回去,算不算没完成任务?
“跟他们没法讲科学,可在宗教场所,讲科学又有点搞笑”。
行李和道长吐槽游客素质不行,不想跟在屁股后面劝说这些不会改变自己的人,这让他觉得自己很暴躁。
道长回答,你以为庙里与世隔绝了吗?修仙修道先修做人,
“人都不会做,怎么能做神仙?”
“这就是修道,它让人变得更智慧。你可以通过学习获得知识,却未必能得到智慧。比如练武——你能看到的是道长手里的铁剑,但修道之人参悟的是内心的慧剑。有了慧剑,才能斩断烦恼。”
在武当山期间,行李写了20多万字的日记,发在了不同的社交平台上,一度让他小火了一把。
但现在回看这些日记,不难发现这些文字里充满了焦虑。
行李本想在2019年12月左右离开,但又听说春节的武当山很热闹,想多待几天。
没想到,突然起来的肾结石发作让他走不了,等真想走时,疫情又爆发了,武当山都被封锁。
隔离期间,行李和整个世界的交集就是抖音上的各种神曲、大家见面口口相传的新闻。
行李没有了以往的乐观,总因为负面信息而焦虑——担心自己在道观里每天和那么多游客接触,会不会被感染?
封山后粮食够不够吃?如果突发疾病,是不是能及时送到山下就医?在物资短缺时期会不会被大家嫌弃?
03
疫情期间,行李感到很失落。
2020年3月,疫情最不稳定时,道观里的大家却乐观得多。行李问他们,为什么不着急。
对方答,“现在正是玉皇大帝在人间查人功过的日子,借助疫情整顿人间;等到正月十五的时候,他就会让天官赐福,世间积德行善的人们都会过上好日子的”。
“你看我们国家现在这么强大,一定能渡过难关的!”
“所以到底是靠玉皇大帝,还是靠政府?”
“靠……靠自己积德行善!命是天定的,运是人为的。尽人事,听天命。你修得一身正气,妖魔鬼怪见到你也会恭恭敬敬的——但行好事,莫问前程!”
几番问答以后,行李忽然意识自己学的人文科学在关键时刻似乎起不到什么实际作用。
既不能通过医学手段帮人解决实际问题,似乎也没办法通过传播思想的方式帮人解答疑惑。
他开始考虑起下山后的事情——武当山的生活不能持续下去,他也暂时没有出家的想法。如果回城里,最好做点具体的事情。
行李考虑过中医,但同学说大多中医培训都是以赚钱为目的,远达不到治病救人的程度,“不害人就不错了”。
他想和外界保留一点弱联系,但又不愿意被朝九晚五的工作捆绑。
行李打起了开书店的主意,那样可以“每天坐在咖啡和烤面包的香气里擦擦柜台、摆摆书架,闲了就弹弹琴,发会呆,在看似漫不经心的角落里体现着生活品位,并和文化圈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联。”
文青的另一个特质结束了他的理想:
穷。
手续繁琐,前期投入太大,加上房屋的商业执照即将过期,有关部门是否允许其继续经营还是未知。
最后,开店理想和现实条件妥协的结果就成了,行李在姥姥姥爷留下来的小平房里开了个小卖部。
实际操作时,胡同里的邻居们却不同意了,一会儿上门说小卖部违建,投诉消防让拆除;一会儿说行李洗澡的水总往院子里流,万一堵了下水道怎么办。
甚至有时行李委托邻居看店,客人来买东西,邻居却故意说不知道去哪儿了。
行李记忆中童年的北京胡同可不是这样。
当时大家一片和气,退休老人们自觉维护胡同治安,小朋友放学回来可以先去邻居家写作业甚至吃饭;谁家买的冬储大白菜送到了,直接堆在院子里就行,绝对一棵也丢不了。
他反思自己,或许是在“首都北京”生活久了的自己习惯了“老死不相往来”的城市社交距离,疏远了胡同里的人情关系,忘了胡同里的“三观”。
虽然邻居没少什么,可行李“多”了,就是得罪他们了。
胡同里的人才不管你来自东北还是河南,去过美国或者阿联酋,也不管你是“张家的儿子”或者“李家的姑爷”。
如果你自视甚高,敢和大爷大妈吹嘘卖弄,那么就算对方祖上三代都是底层百姓,也不妨碍他心里有一万个理由排挤你。
最后,行李放低姿态,给所有来买东西的邻居最低价,这才算是把小卖部给开起来了。
04
行李读过《乡土中国》,可在很长时间里,行李却不理解这就是现实。
经历过武当山和小卖部,行李忽然意识到,不论是穿军装、道袍、还是西装,他所遇到的大部分国人在骨子里依然苦于解决温饱问题,这就是中国的乡土人情。
他们大多从逻辑的角度看问题,依靠先天的情感和非理性,
不靠“因为……所以”来行事,而是“我愿意/我觉得……所以”。
在民族大学读人类学时,老师和行李讲公民精神、法治精神,可在具体生活中,这些理论往往解决不了问题。
你跟他说这个,他反而觉得你在无事生非,要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必须懂得在社会关系上多付出。
想通了这一点,行李渐渐明白了,为什么过去常会感到愤怒,因为他不过是凡人而已——
有控制欲、却没有控制力,这种乏力感才最致命。
几个月前,某部队单位招文职,亲戚推荐行李参加考试,只有三五人报考,以行李的成绩,应该没问题。考试那天早晨,起床时,行李反复犹豫,究竟该不该去呢?最终,行李还是没去。
又有一阵子,行李想去摆摊卖煎饼,但父亲不同意,觉得这不是北京人该干的事,
“这让我怎么面对街坊邻居呢?”
对于开小卖店,父亲也一直不支持,行李恼火了,说“你对你们现在的生活满意吗?如果不满意的话,我按你们的路走,30年后不照样是不满意?”
在好多人眼中,行李有“北京土著”、“国企呆过”、“人类学硕士”等成功人士的标签,但现在却混成这样,似乎又是世俗眼里不折不扣的Loser。
可是,人生难道应该只有一种定义吗?行李对此感到质疑。
他记得几年前,还在出版社做编辑时常坐4号线地铁回家。
那条路行李走了无数遍,但就是有一天忽然意识到地铁上的每个人都那么好、长得那么漂亮,可每天却和他一样乏味单调。
无非是上班偷着骂甲方、骂领导,中午骂食堂,下午接着偷着骂甲方、骂领导,晚上刷会儿抖音、淘宝,一天就过去了……
他们明明有很多选择,却有如此一致的焦虑。
行李很疑惑,这种同质化的人生,又有什么意思呢?人人都想往上,却没有一个退出机制。
行李选择了武当山和小卖部,不过是主动寻找一种不让自己焦虑的退出通路。人总有一种可能性,能够“不思上进”地活着。
但“不思上进”也是有代价的。他很认真地思考过小卖店存活下来的必要,行李算过一笔账,小卖部从去年6月份到现在,
共赚了6千元钱,平均每个月1千元。
胡同里的小朋友倒是常在小卖部门口玩,有时候敲门敲窗和行李“躲猫猫”,还顺手撕了门口的海报。
行李没哄过孩子,但觉得既不能呵斥他们,也不能装看不见。后来,他试着用薯片、饼干逗小朋友,把他们馋得流口水,扭头跑回家问爷爷奶奶要钱买。
开小卖部赚不了几个钱,但对这些孩子来说,
小卖部或许是童年时候“天堂”般的存在。
而对行李来说,开小卖部的每一天都能重拾童年的愉快回忆,这也就够了。
现在,行李快35岁了,没结婚,也没女朋友。他觉得成家是很麻烦的事,不能为解决一个问题,落入更大的问题中。
一个人的孤独乘以二,又有什么意义呢?
至于未来会如何,行李依然想学习,但想学那些能帮助人们、更切实一点的专业,但这专业到底是什么,他也没有答案,也不着急去找这个答案。


